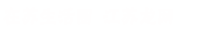最终 , 人们对歌曲的不满 , 指向了创作者 。
从“谢谢你”到“对不起”在这个春天 , 大家都对《听我说谢谢你》PTSD了 。 一首普普通通的儿歌 , 何以至此?
大家对于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不适感 , 最初是一种情感带入下的“尴尬” 。 面对儿童在核酸检测现场跳舞的视频 , 许多网友瞬间梦回在家庭聚会上被父母强迫表演个节目的童年 , “脚趾抓地”成了许多网友的共同情感体验 。
然而 , 共情以后带来的“尴尬” , 还远不至于令网友集体抵制这首歌曲 。 更深层的价值对立 , 才是网友厌恶歌曲的关键 。
即便将场景移至核酸检测现场 , 家长们此举的目的还是让孩子表演个节目、炫耀孩子的才艺 , 这样的行为是属于“家庭”这一场域的 , 讲求的也是轻松、愉快;而集体核酸检测是属于“集体”场域的 , 讲求的是高效、严肃 。
行为与场景的不适配 , 也就造就了价值的冲突 。 “个体”与“集体”的对立、“轻松”与“高效”的对立 , 让网友在尴尬之上更生出抵制与反感的情绪 。 再加上 , 对感染风险、作秀之嫌的诘问 , 公众的不满情绪需要一个窗口 , 而在缺乏思考的无差别攻击下 , 创作者就躺了枪 。
事实上 , 歌曲的创作和传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 。 歌曲由李昕融一家创作并演唱后 , 进入流媒体平台 。 随后 , 歌曲如何传播、如何被诠释和解读、歌曲内涵有哪些延伸 , 实际上都不是创作者所能左右的 。 换言之 , 歌曲在“二创”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该由创作者担责 。
在为歌曲的不当使用而道歉后 , 李凯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“宁愿这首歌没有火起来” , 但是“不后悔写了这样一首歌” 。 创作者一家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理解和支持 , 他们表示歌曲本身不存在问题 , 是滥用歌曲的错 。
然而 , 李凯稠本以为回应可以平息针对家人的网络暴力 , 却依旧不乏网友指责这一家人在歌曲热度下降时出来“蹭热度” 。 对此 , 樊桐舟觉得十分无奈 , “互联网就是这样 , 每个人看到的内容、理解的方式都不同 , 作为作者只能接受 。 ”
巧合的是 , 在道歉视频发布当天晚上 , 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中唱了《听我说谢谢你》 。 许多主流媒体转发了演唱的视频 , 使用的标签是#听我说谢谢你的正确打开方式# 。
樊桐舟在采访中表示 , 这是对歌曲的一种帮助和鼓励 , 对于他们一家而言是“一剂强心针” 。 这一刻 , 这首儿歌冲出地球、走向宇宙 。 在高国民度的大事件的加成下 , 民族自豪感终于给在舆论漩涡中的《听我说谢谢你》带来了“庇佑” 。
“相当于把这首歌扶正了 。 ”樊桐舟说 。
从“反感”到“反思”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写道 , “在这个时代 , 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 。 ”
在他看来 , 在电子媒介勾画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 , 再残忍的谋杀、再具破坏力的地震、再严重的政治错误 , 都在娱乐化的倾向中稍纵即逝 , 很快就将被引人入胜的球赛和音乐会所取代 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 , 媒介不再提供信息 , 而是提供情绪 。
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国民性议题面前 , 我们应当很欣慰地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理性的回潮 , 没有像波兹曼的预言一样用娱乐消解苦难 。 从《听我说谢谢你》手势舞带来的质疑 , 到全民叫停一场载歌载舞的抗疫晚会 , 当娱乐化的内容裹挟在更为严肃的社会性议题之中 , 网民们自发地调整了注意力的分配 , 将关注点放在更重要的内容上 。
然而 , 这种理性始终还是有限的 。 公众很快就将一切推向另一个极端 , 对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创作者提出了荒谬的“道德要求” 。
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, 1993年的民众对摄影师凯文·卡特作品《饥饿的苏丹》的质疑 。
人们痛斥凯文没有将饥饿的女孩从秃鹫的口中拯救出来 , 痛斥这个摄影师冷血、见死不救 。 即便凯文多次公开解释秃鹫没有攻击小女孩 , 在按下快门键后秃鹫随之飞走 , 小女孩也跟着前来领取救济粮的母亲回家 ,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。
终于 , 在作品问世一年后 , 凯文选择烧炭自尽 , 结束了这些猜疑和指责 。
虽然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影响和结果远不及《饥饿的苏丹》来得残忍和令人难以接受 , 但是本质上他们都揭露了一个事实 , 作品一旦出版发行 , 它便脱离了原作者而存在 。 它被误读被滥用 , 其实都与原作者无关 , 但是原作者却需要对“正义的舆论”负责 。
推荐阅读
- 李克勤|炎明熹一鸣惊人,真假音转换丝滑又好听,李克勤有点小骄傲
- |为什么说听港乐长大的男女,都很幸运?
- 祝卿好|《祝卿好》沈昱派人去听大婚弟弟的房门,他是有什么特殊癖好?
- 李光洙|闯祸!李光洙没答对「女友李先彬的歌」低头忏悔:我真的每天听…
- 周深|听了周深的歌,看到他在芒果台的大不同,才知他的“嘴”有多神奇
- 周深|心心念念的《彼岸花》终于上线,周深又一首抚慰心灵的歌曲,好听
- 韩红|王一博为韩红新歌助力,韩红现身评论区:一宝,谢谢你的支持
- 唐嫣|“自甘堕落”唐嫣:捡漏争议品牌遭抵制,为何不听劝阻自毁声誉?
- 肖战|花海故事你听过吗?某导演再次内涵,肖战百度搜索指数第一
- 周深|《祝卿好》周深在线撒狗粮,献唱主题曲,《卿卿》收听率秒破千万